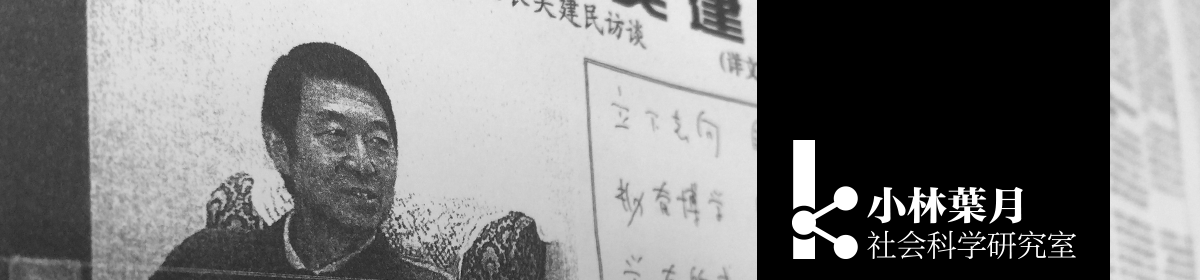我平时不太乐意出席各种讲座活动,因而错过了一些和吴建民院长直接见面的机会。我印象中唯一一次直接见到他,是在2015年北京模拟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上。我坐在礼堂最远端的中控室里,隔着厚厚的隔音玻璃,看着吴先生给台下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讲人生的经验。
看得出,来自全国各地的、或许想成为外交官的小朋友大朋友们,还是比较欣赏吴先生的:毕竟吴先生出版的几本外交案例的专著,卖得还不错。
在学院里面好像也是如此。在学院里提到赵先生时,学生们会鼓掌欢迎;而提到吴先生时,鼓掌的音量似乎会大一些。
也许这和吴院长更加强烈的个人印象有关:赵先生退休后,就很少再到沙河校区露面了;而吴先生直到今年三月末,都还愿意回到外交学院,为年轻人们带来一场讲座——他甚至愿意回答年轻人的一些相当尖锐的问题,全然不顾自己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身份(当然,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一场内部交流活动,直到演讲原文出现在网上,又引发了和胡锡进先生的一番争论,而这又是后话了)。
吴先生说话的方式和内容,也更平实亲切一些。我曾做过外交学院校报《外交人》的主编,因而得以能到十几年前的故纸堆里,去翻一翻当时的话。吴先生2003年夏天初到任时,接受了报社一次专访。与其他先生不太一样的是,吴先生似乎是把学生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。他在第一个回答中就这样讲:
“……我想我们学校是培养精英的。我们招生的生源比较好的,但是招生比较好,能不能成才?从学校来讲,我们就是要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氛围……要大家增长见识。中国的精英是怎么样的?世界的精英是怎么样的?”
这点到了外交学院学生的痛处。直到2016年,外交学院的生源质量在全国都位列 Top 20 甚至 Top 10,力压一大片211、985高校;然而在出产的学生质量榜单上,似乎又难寻踪迹了。
吴先生到任以来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开设了“外交学院论坛”。光是开始的2003年9月到12月,就陆续有前外长钱其琛、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、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以及达沃斯论坛创立者克劳斯·施瓦布等诸多与外交实务和个人修养相关的各行业领袖莅临。而外交学院论坛举办的频率,在吴先生在任的五年内一直很高。甚至吴先生的夫人、原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施燕华大使,都被他“请过来”开讲座——学生们也真的想学习这种外交实务的经验和教训。
而且吴先生是真的想讲点东西,做点事情。
有时学院的学生会自嘲说,在秦先生之前,外交学院院长这个职位就像是“外交官退休前的休息点”。而吴先生似乎不这么想。在吴先生的任内,外交学院签订了建设新校区的协议,将英文校名由 Foreign Affairs College 改为了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(吴先生说,这一改动是为了促成发展和国际交往;至于周恩来题字的“外交学院”四个字,“我不想改”),更为学生们打开了无数扇认识世界的窗口。吴先生自己甚至都在学院里开了两门选修课,其中一门名为《交流学》的课,也一直留到了今天(遗憾的是,如今的课程内容,与当年吴先生讲述的内容已经不太一样了)。
吴先生也在各种场合,不断地向学生强调要有大局观。2005年小泉内阁参拜靖国神社,吴先生甚至拉着包括秦先生在内的所有学院领导(当时秦先生还是副院长),一齐搞了一个面向学生的问答报告会,专门讲应当如何理解东北亚局势,反复叮嘱学生分清“爱国”和“误国”、分清合法和违法。“我到一个大学去演讲,校领导让我讲出同学对日本的仇恨,又不能出轨。这难道要我煽动仇恨?这就是对大局的不理解。”
不得不说,这话到如今,依然有重复的必要——而且很有必要。仇恨一个国家,毕竟不是外交应该做的事情。
况且,我们应当记得吴先生是敢讲的。
2003年,在对《外交人》的访谈中最后,吴先生说:学生报纸有两条很重要;而比起弘扬正气,排在前面的应该是考虑读者、写学生爱看的东西。坊间愿意评价吴先生是“鸽派”,我倒是愿意说,吴先生在一些问题上,开明程度与如今相比,却是已经“激进”到了一定水平啊。
本文系为香港端传媒撰写的《吴建民,和平外交路上的孤独背影》一文的节选原稿,最终发表时有改动。